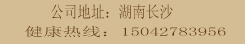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疲劳性骨折 > 疲劳骨折诊断 > 全民抗疫时期见闻战胜恐惧,且看经
当前位置: 疲劳性骨折 > 疲劳骨折诊断 > 全民抗疫时期见闻战胜恐惧,且看经

![]() 当前位置: 疲劳性骨折 > 疲劳骨折诊断 > 全民抗疫时期见闻战胜恐惧,且看经
当前位置: 疲劳性骨折 > 疲劳骨折诊断 > 全民抗疫时期见闻战胜恐惧,且看经
庚子年不易。
年1月1日,我和家人前往日本短期休假,顺道在神户大学做讲座。没过几天,突发的武汉肺炎疫情,打乱了预定的回程时间,于是决定再滞留几日。然而,身在日本,心系国内疫情,睁开眼睛,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无一不是关于处于全国总动员的武汉肺炎“阻击战”。此次疫情正在演变为一场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
过几天就要回国了。朋友告诉说,今年的最佳礼物非口罩莫属。于是,去东京的商店购买口罩,发现因国人狂购,大多数商店不得不限购了,以保障更多人能够买到。之后来到名古屋,以为可以多买点,结果仍然是每人限购5包。看来,恐惧已越过国界,开始在日本蔓延.....新闻上说,美国华人社区的恐慌行为也大同小异,只是还没限购。
观察亲朋好友的当前反应,好像除了武汉肺炎病毒,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不值一谈,似乎要社会上下“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清除这个瘟神,才能安心度日。手机刷屏各路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已经成为当下人们惶恐中最忙碌的事。民众恐慌情绪日益剧增,令人喘不过气来,已难以分清究竟多少是关于肺炎病毒的理性认知,多少源于众人的集体恐惧本身。
此次新冠病毒究竟有多严重,对人类生命的绝对威胁到底有多大,截止目前,无人确知,也许永远也无法知晓。因为它是个不确定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物种,没有已知的风险概率函数可资分析;又因为个人、社会、政府交叉进行举国上下的各种干预,对其开展干预评估和科学认知的归因分析变得几乎不可能。
不过,作为健康经济学家,我仍然好奇人类在过去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或不确定性事件的经验行为,是否能够映射当前人们的认知,从而对采取更为理性和有效的防控措施有所启示。从历史上看,人类最近一次的灾难性公共卫生事件当属-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甲流),它导致全球超过5亿人感染,估计有-多万人丧生,死亡率高达6%左右。进一步分析发现,超过百万级死亡的地域大多都分布在亚非拉的贫穷国家,当时这些国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诊疗能力极度有限,应该是导致死亡率高的主因。如果进行同期疾病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当时全球平均婴儿年死亡率高达26.9%,年均婴儿死亡总数为多万,两年死亡也超过多万。如今,得益于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全球婴儿死亡率已大幅降低到2.9%以下。不难想象,如果那次大型甲流发生在今天,结局应该大不相同。事实上,、相继发生的H1N1甲流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相对更低正表明了这一点。
再回到当下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人们在初期极度恐慌其难以琢磨和逃避的不确定风险,自然无可非议。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常识:即面对某些可以部分防控的常见疾病,其实际死亡风险也不小。根据国家疾控中心9年底的官方统计:中国每年常规流感超额致死人数为8.8万。那么,保守估计,流感高发季节的平均每月致死人数不会低于1万。因此,就实际发生的灾难性结果而言,常规流感仍然是目前新冠病毒致死规模的百倍量级。
还有,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大家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也在增加。1月28日,我曾仔细看了美国卫生部会同CDC主任和顶尖流行病科学家共同召开的官方发布会,根据评估大型传染性疾病严重程度的三个核心指标(致死率、传染率、潜伏期),美国卫生部长AlexAzar报告了武汉肺炎的致死率在%左右,并且因为大量较轻的患者未能检出,这个数字仍然具有较大的高估偏误。事实上,今天0日公布的全国死亡率已降到2.2%。第二是传染率,根据目前公开发布的科学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平均传染人数为1.5-.5(即R0值),1月29日刚刚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的估计值为2.2,均显著低于我们熟知的几大传染病:麻疹(12-20);天花(.5-7);流感(2-4);SARS(2-5)。第三,潜伏期,目前中外专家一致的估计是不超过14天,因此大多患者应该接近和过了潜伏期。据此,如果感染率不再增加,有专家称这可能预示着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平稳或下行的拐点。
话虽如此,我也时有困惑:以上数据都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武汉肺炎病毒是全新的物种,具有未知的不确定性,谁能保证这个巨兽不会突然完全失控、肆虐人类呢?不过,对于还未曾发生的事,谁也无法给出肯定答案,恐惧正是来源于这种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就该“不惜任何代价”防范可能具有灾难性的小概率事件呢?封城,作为重灾区的武汉也许是不得已的权宜之举,但所有其他城市又该如何采取诸如停产、停运等对社会经济的“休克式”疗法呢?对此,我想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上下足够的全面思考和从长计议,毕竟我们还有太多其他的重要工作需要进行。
面对全新风险,有危机意识、争分夺秒,积极作为本不错,但一事会伴生多事,顾此失彼的麻烦可能更大。其实,不仅是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即使在社会事务与企业管理中,但凡涉及处理不确定性事件的责权比较大时,当事人往往因为恐惧、无知、或免责意识而选择过度校正,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最终得由大家一起买单。因此,凡事“贵在有度”,所谓科学决策就是要对不同行动选择的利弊进行全面、客观的权衡,从而提高集体行为的理性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类“不惜任何代价”去规避某个风险或解决一个问题,既不明智也不现实。因为人类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事情的资源投入都将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受到经济学“边际效益下降”铁律的约束。如果“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为眼下一件事配置过多的资源,必然付出挤占其他资源从而增加更大风险的代价。有人说,生命胜于一切,生命无价。真是这样吗?如果生命无价,如何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说?在现实社会中,为何还有不少人愿意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只要能得到足够高的补偿性工资呢?答案在于经济学的道理:勇夫还有包括养家糊口在内的其他诸多经济目标诉求,所以考虑并权衡高风险工作的经济得失就是理性选择的表现。人类的生命健康固然重要,但得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反过来,更好的生命健康又促进经济增长。
纵观人类发展的演进,其实就是伴随风险成长的历程:与风险共生,并逐渐认识和降低威胁生命的新旧风险。尤其是农业文明以来,人类与传染病的抗争可以说是自身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不仅如此,非传染性的风险也不陌生,并越来越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以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为例,国内交通事故每月致死约1万人,政府不断提高交通安全要求和出台新规章,但并未完全限制出行;药物不良反应每月致死为约1.5万人,医院不断加强用药安全措施和提高医疗水平,但并未全面干预个人用药;雾霾等空气污染致死率更高,人们不断改善空气质量,但除了举办大型国事外,并未全面停止排污的种种生产活动。简言之,人们面对长期伴随的众多威胁生命的风险活动,除了采取理性、必要的防护措施,并未自我恐惧,社会秩序并未打乱。其实,只要经济活动不停,日子就能如常,并还能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然而,如何解释上述的人类悖论行为?也许生物行为心理学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人类物种对习以为常的风险逐渐熟悉,并学会淡定应对,行为科学称之为“预警疲劳(alarmfatigue);但对未知物种的侵袭本能反应一般是超度紧张,从而采取超度行动,以期规避损失(lossaversion),其中当然不乏理性和非理性的交互作用。有意思的是,在应对新旧物种入侵时,人类并不比动物理性多少:接受与熟悉物种的共生共存,虽然风险依旧;对新物种的到访则极尽全力要么除之,要么逃之,或吓尿自己。这让我再次思考人类与低等动物的本质区别。如果说人和动物都具有贪生怕死的本能,而根本区别在于人类能够理性思考的话,那么人类似乎并未总是很好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尤其是在处理突发应急风险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原始本能所致的恐惧往往占据上风。不幸的是,恐惧正是愚蠢行为和放大灾难的罪魁祸首。
如同自然界的恐惧行为一样,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也不乏因为自我恐惧而作茧自缚。始于年的那场全球经济大危机,尽管导致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人们因恐慌而酿成全社会的银行挤兑,是造成美国银行业塌方式倒闭的决定性原因,并从而引发投资、就业、收入的大规模恶性连锁反应。所以,为了阻止经济大规模的持续下滑,唯有从消除众人的恐惧、恢复信心开始。对此,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年初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盲目冲动、毫无缘由的恐惧,可以使人们转退为进所需的努力全部丧失效力”。
很多时候,恐惧源于人们对事物的不了解和不确定性,而非事物本身。一个社会的成熟在于如何控制危机中的恐惧程度,需要淡定应对而不慌乱,全面考虑而不顾此失彼。今天的中国,正在历经跨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不断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要求随着中国规模的增大而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其对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有效流动要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此,在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阻击战”中,如何全面科学的权衡城市管控和资源流动的利弊得失,是考验各级政府决策和社会大众行为是否能够更为理性、成熟的重大挑战和难得的学习契机,也是一道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的重大命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国恩教授写于年1月0日)
经典的病例——全民抗疫时期的见闻
最近几天,疫情报告的病例数与日俱增,不仅超过了非典的确诊病人总数,而且每日新增病人也是有增无减;截至目前,许多人呆在家里时间已经超过了一周,恐慌和焦虑的心情看来也在不断积累,大有惊弓之鸟的态势。
昨日,有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一个消息,称在试验用双黄连可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病人。瞬息之间,网上所有的双黄连口服液都卖空了,据说连兽用带双黄连的药品都买不到了。今日一大早,医院值班,路过两三个药店,都见到有三五成群的顾客在其中逗留,路遇的一对老年夫妻急匆匆走过,他们在急迫地奔向药店,口中商讨着说:就看看有没有口罩和双黄连。我想,在这个万店都关门的时候,药店里的人们,不外乎也是买口罩或者双黄连的吧。
这有点类似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或者消毒液。网上有人调侃说,就是最火爆的带货网红,也远远不如这恐慌性销售,瞬间就能清库存;想来今后经济学又多了一个研究领域,专门研究恐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是的,这种买中成药囤积或者预防病毒感染,其实多半是在交智商税,极不靠谱。实际上,今日记者电话询问了上海药研所的有关人士,他们对此也是语焉不详,表示只是在初步研究,并达不到用于治疗病人或者推荐使用的程度,更谈不上可以用于预防。
有时我觉得很纳闷,许多人平时对预防疾病是很不上心的,比如你告诉他戒烟限酒可以预防慢性疾病,或者说运动锻炼能够增强身体抵抗力,他多半是不会听你的,或者是听了就当耳边风过去了;但是在这种焦虑和恐慌的时候,他就特别相信预防了,即使权威们都说了没有预防药物,他还是会听信不靠谱的或者貌似合理的传言甚至谣言,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也许这就是当下许多所谓团销或者传销盛行的原因,因为他们总是让参与者有危机感、紧迫感,总是想办法制造一种焦虑与恐惧的心理环境,于是很多人就乐在其中了。
这种现象如此广泛存在,看来所谓恐慌经济学研究真有存在的道理呢,有没有人来仔细研究一下:恐慌刺激消费的基本原理、表现形式、适用人群还有怎么促进经济增长?哈哈,可以研究的的确是不少哦。
从这个事件出发,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问题。比如那些貌似权威的研究机构该怎么向公众发布研究成果,是哗众取宠博眼球,还是踏实做出真正靠谱的成果再说?要知道这个上海药物所已经出过一次虚名了,就是他们宣布的那个划时代的治疗老年痴呆药物,结果被揭出了许多难堪的老底,什么论文造假、夸大其词之类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向钱看厚里赚心态支配下,靠流量靠
转载请注明:http://www.pilaoxingguzhe.com/pzzd/7361.html